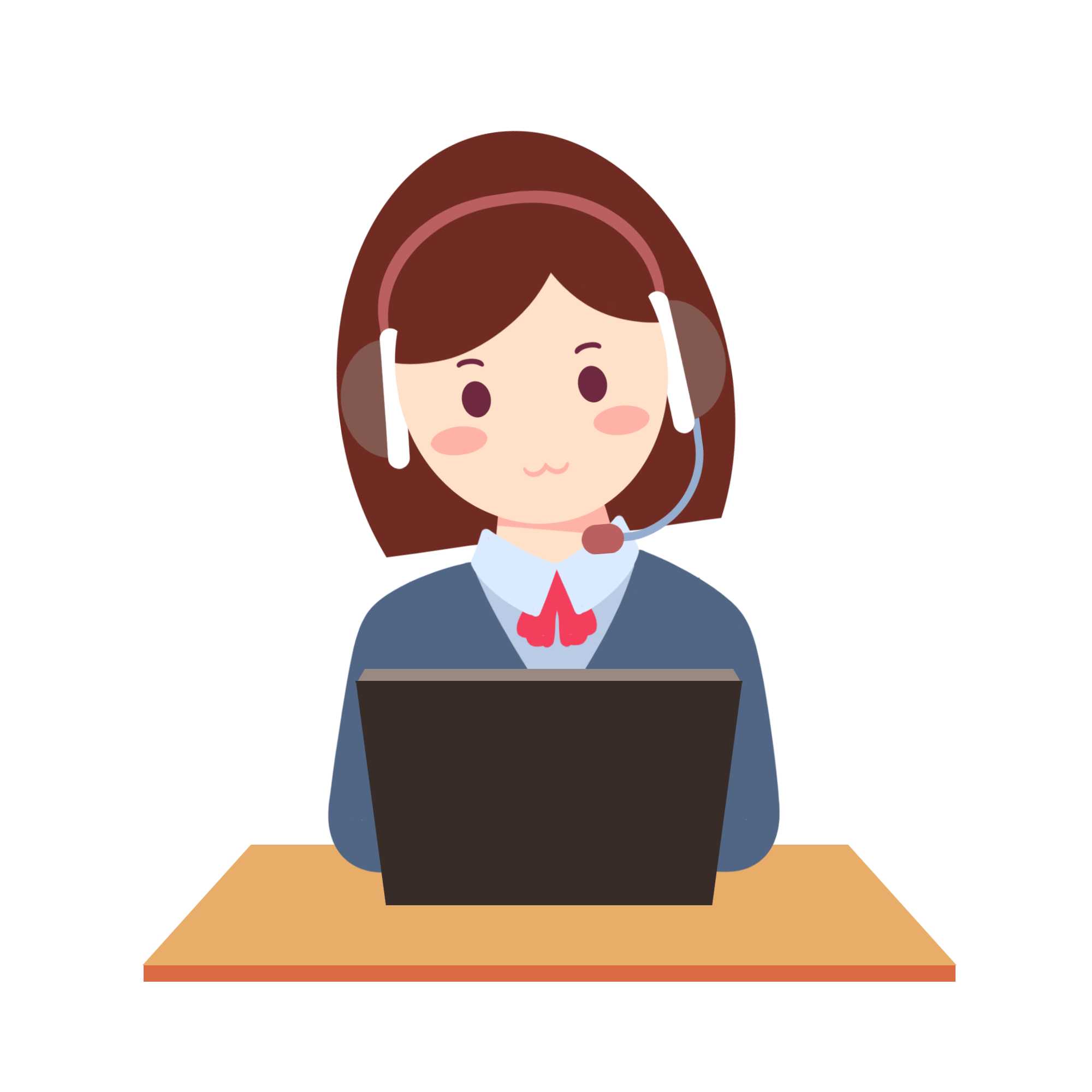11332人
11332人我是秋也,一名确诊八个多月,实际上病了八年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八年的前半段里,自我伤害、离家出走、对每一个爱我的人恶语相向,但我至少还能感觉到我活着。八年的后半段里,我每一日都计划着对自己的谋杀。
01
妈妈的强势和控制欲让我没有一点安全感。她偷看过我压在书堆最底层的日记,深夜里翻我的书包,并且不以为耻将此作为饭后的谈资。
父母对妹妹的偏爱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每次我与妹妹争吵,他们总扮演着她的保护者,却没有一个人为我说话。“妹妹还小,你是姐姐,要让着她。”这句话到现在都是我的梦魇。他们总紧紧地护着妹妹,我站在他们对面,像一个陌生人。
作为家里诞生的第一个孩子,我自然被寄予了所有人的厚望。可是并没有人想过,一个小女孩要怎样做才能完成几代人的期许。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说着爱我可我却感觉不到,明明呆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房子里我却好像时时刻刻淋着瓢泼大雨。
你看,世界这么大,可我无处可去。
最后,我精心计划了一场完美又恶毒的自杀。只是没有进行到最后一步——爸爸接妹妹放学回来了,妹妹笑眯眯地问我,她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吃我买的蛋糕。我笑着说可以,用那把本来要自杀的刀给她切了蛋糕。
我是那么恨,又那么爱每一个人。只是从那一天起,就算自杀的念头再强烈,我也没有计划过自己的离去。只要活着,那一切就都有转机。
02
我是一个很惨的小孩。每一个听完我的故事的人都这么说。
2019年7月28日,我第一次去正式的、全自治区最权威的精神卫生中心看病。我一个人去的,那一年我十七周岁,所以医生拒绝为我进行一系列的身体检查,她只告诉我,我正处于抑郁状态中,但不能确定是否达到了患病的程度。她让我带父母来,我拒绝了。
临走的时候那位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其实你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孩子。你就像一棵被石头压着的草,一直在独立地向上长。知道吗,草生长的力量,足以顶开压着它重石。”
我笑了笑,认为自己并不是那样一棵好草。我只是荒野中濒死的一株枯草,和万万千千最普通的野草一样。
同年,我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里迎来了第一缕曙光。心理老师和我讲了萨提亚的“五大自由”——自由地听,自由地看,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去感受。这五大自由仿佛一柄利刃,为我破开一道迷障。第一次有一缕晨光从缺口中漏出来,照在我身上。
2020年,是我厌世情绪最高涨的一年,也是我开始出现躯体化的一年。
不知道哪天起,我的手开始控制不住地颤抖;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呕吐;上一秒说过的话下一秒就会忘记,说着说着头脑就一片空白,只能悻悻地闭上嘴巴。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做任何事只想安静地躺着,但又睡不着觉,一个星期最少的时候只能睡八个小时。
渐渐的,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从榜首落到了名单最底下。最后,我高考的成绩连二本线都没上。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父母十几年来对我最多的失望。
我很多时候都在想,应该如何形容我父母当时的感觉呢?
大概就是,你种了一棵树,一直以来精心栽培,施肥除虫样样不落。这棵树也如你所想的那般生长着:树干笔挺,高耸入云;树冠繁大,枝繁叶茂。于是你心里认为,这棵树结的果一定又大又甜。你等啊等,等到秋天来了,迫不及待地摘了一个果子吃。一口咬下去,是从未想过的又酸又涩,低头一看,还有半只干瘪的虫子。
你又恶心又愤怒地踹了树一脚,没想到在树干上踹出个通心大窟窿。树被你踹的晃了晃,“轰隆”一声,断了塌了。你骂了一声,说早知道就不种这棵树了。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些年的辛苦都付诸东流,一甩袖子离开了,全然忘了这些年在树荫下乘凉的那些日子。
其实只要你凑近一瞧就能发现——表面上光鲜亮丽的一颗树,早就从心子里被虫吃了干干净净,盘根错节的根早就腐烂了。
我就是那棵树。
03
2021年三月,我在大学所在的城市的精神卫生中心开始了我第二次正式的医院之旅。
这一次,我做了许多量表,做了血检、脑部的检查、心电图,结果为重度抑郁和严重焦虑。医生建议我吃药治疗,我拒绝了。因为,我没有钱。
同年的五月,我觉得再不看病,我就要活不下去了。纠结了很久很久,写了一封信发给了妈妈,顺便附上了诊断书。妈妈告诉我,等我回来,就带我去治病。妹妹偷偷告诉我,父母哭了很久很久,他们并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不开心。
七月,放假在家的一个晚上,我很认真地要求妈妈带我去看病,我真的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溺死在漆黑的海里。第二天,去了我第一次去的精神卫生中心,只是这回父母都陪着我。
经过量表和体检后,医生和我进行了一些交流。这位温柔的女医生看了我许久说:“孩子,你好似在陈述别人的故事。”我心想:因为这些话,我已经在心里对自己说了千千万万遍了,我早已麻木到没有一滴眼泪。
最后拿到诊断书的时候,父母都沉默了。妈妈不愿意让我看诊断书,她紧紧地攥着那几张纸,苍白无力地安慰着我。其实不看我也知道答案。
医生开了药给我,吃了一个月却不见效果。复诊时医生仔细询问了我的情况,最后得出了结论——是双相情感障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简单了解过后担忧又释然。
我坚定地选择继续吃药治疗。我吃的第一组药是文拉法辛和丙戊酸钠。吃了一段时间,我的情况慢慢稳定了下来,但药物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发胖嗜睡、手抖。我想了很久,为了充满希望和积极的活着,付出的这一点点代价我能接受,世间难得两全法,我明白。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情绪虽然稳定了下来,可是我的记忆力还是那么的差,这不是我想要的。
随着文拉法辛让我险些转躁,我又换了药——拉莫三嗪和安非他酮。换药的头几天,我似乎对拉莫三嗪有一点过敏浑身刺挠。每一天我都仔细观察着我的皮肤,我不想放弃这个药,我也不想放弃我自己。还好没有过敏。
我越来越稳定,情况一天比一天更好。我的脑子比以前灵光了许多,学东西越来越快,思维也开始变得活跃;没那么容易发脾气了,言语也温和了许多;说话渐渐有了逻辑,从前消失的灵感也正一点一点的回到我的笔下;我不再懒洋洋的毫无行动力,变得上进许多;我不再旷课,努力做到成绩更好。
我感觉得到,我的羽翼正在变得丰满起来,我也一天比一天更快乐,更有期待。
有一句话说,“如果没有见过光明,我本可以忍受黑暗。”我也一样。我见过了光明,坦荡地站在青天白日里,便再也不想匍匐在黑暗之中蝺蝺独行了。我想要自由且勇敢,热烈而诚恳,清白明朗的活在地动惊天里。
我其实并不知道我会不会完全痊愈,会的话最好,不会也没关系,我会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普通人,一定会好好的活着。
我不是枯草,我会顶开那颗重石,长得和周围的草一样好。
(文章图源:摄图网)
本内容版权归好心情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本内容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作为疾病诊断及治疗依据,请谨慎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