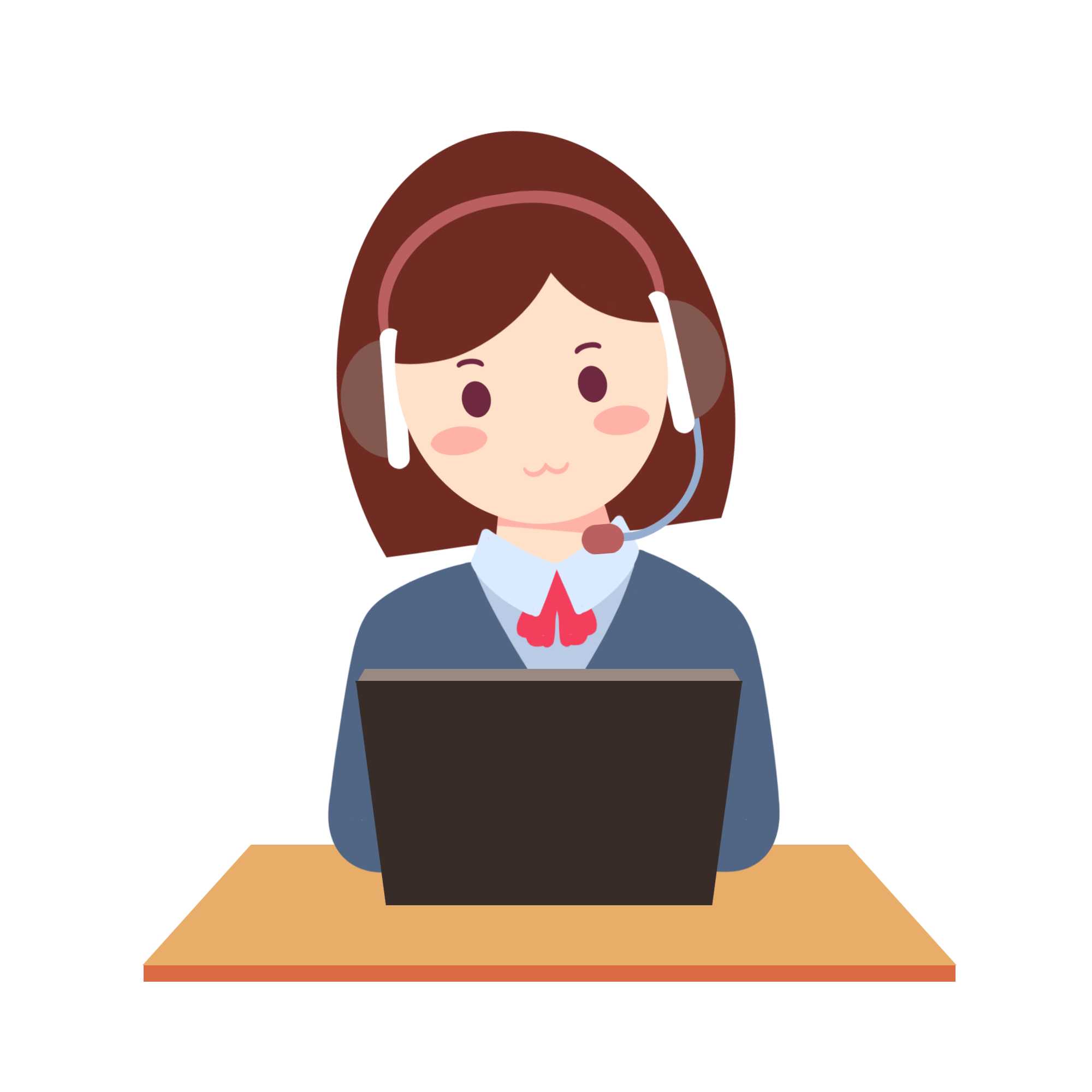12492人
12492人回首再看一眼牢固的大铁门,就此别过,不要再进来了罢。
想起将近一个月前,还没进去时,我和辅导员在此说笑。
“我喜欢他的名字,甘照宇。”
“怎么说?”
“照亮宇宙!”
“喔!”
“不像我的名字,畅,他们希望我的人生——顺畅。”
我俩忍不住大笑起来,哪里顺畅,否则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精神科病区的门外。
01
“是双相。”
“怎么可能!我没有他们疯狂购物那些症状!”
“喝醉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醉了。”
甘照宇医生随手拿起一张其他患者的报到单,翻到背面的空白,他画出一条剧烈起伏的波浪线,完了,我知道我完了,那是双相情感障碍的心境图表,也是我的心境图表。他继续解释到:“首先,你的情绪不稳定。其次,抗抑郁药对你不起作用。”
“圣约翰草提取物片,那是植物药嘛。”我还想再挣扎一下,但他没有理会我。
“然后,你的抑郁症状不典型。有两极化的特征,既嗜睡又失眠,既厌食又暴食;抑郁有季节性,秋冬抑郁,春夏自行缓解。”
他说的没错,我也一直怀疑自己的抑郁哪里有问题,比如我就没有抑郁症典型的“晨重暮轻”,我经常是起床还好但是到傍晚坏了,我的病情该叫“晨轻暮重”才对。2021年5月我看韩剧《窥探》忽然文思泉涌,那些艺术上的手法我一下子都看懂了,于是在知乎上疯狂写剧评,为了写剧评我买了本《天生变态狂》,书中作者还患有“躁郁症”,自此我就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轻躁狂”,看到甘照宇医生的简介上写的很擅长诊治双相,阴差阳错“捡”到了他的号我还有些窃喜,可这不妨碍我继续瞒报躁狂病史,毕竟,谁又会真的想自己是重性精神病呢,重性精神病是要上报的,跟一辈子。
我的心境障碍问卷得分是一个硕大的零——有点假了,问诊期间含糊其辞反复瞒报——没有瞒过。
“那这次怎么写?”我的确很关心重精这回事,病耻感让我在一个多月前的就医表现得更不真诚,“焦虑状态”的误诊害得我病情加重。
“先写得笼统一点喽。”病历上写的是心境[情感]障碍,在过去的诊断标准中,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同属心境障碍,是为笼统,不必上报。
“吃药能缓解躯体化症状吗?”纷繁多样的躯体化症状折磨着我,让我觉得我的神经系统已经完了,治不好了。
“能啊。”不知为什么,甘医生说话总是让人觉得很安心。
“不用再做物理测量了吗?”我还想挣扎一下,万一呢,万一不是呢。
“如果你想快点确认,可以住院。”
“那就不用了。”住院要花钱,可我们家已经在贷款了,因为在打官司。从2015年开始的一系列案子,那时有一个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病史的亲人跳楼身亡,精神障碍是我们家族的诅咒。
我拿着病历和处方笺走出诊室,人有些恍惚,那是2021年11月1日,我毕生难忘的一天。去门诊西药房取药,阿立哌唑口崩片,深蓝色,小巧的一盒,我不知道它能给我带来多少改变,但眼下不吃是不行了,不吃我可能会死,我几乎每天都会想死,剧烈的“抑郁发作”(现在看来,有些快速循环和混合发作),太痛苦难熬了,每周都有三四天躺到天亮,一个人那么孤独,就仿佛宇宙中只有我在漂浮,不想死是不可能的。如今终于出现一根稻草,除了抓住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吃药吧,今晚就吃药吧,也不要去惧怕什么副作用了。
走出医院的大门,积压8年的情绪终于决堤。
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是变成了这样?
02
小时候沈阳优秀小学生都会被选拔到少儿部,我考上了少儿部,为此我甚至在小学五年级就学完了初中物理。偏科,然后成绩一落千丈,没有留下,那一届少儿部出了个16岁的沈阳市理科状元。而我去了初中部常态班,但学习进度仍然大幅领先于其他中学,比如,在初二时我答高考英语卷纸就可以考一百三十多分(满分150),到高考时分数来到了143(全省最高分145)。
算上少儿部那一年,我在xx学校待了7年。
高度恶性竞争会让人性变得扭曲,小孩子的恶也是纯粹的。
高一时,有朋友在背后说我:“学文的都是精神病,畅就是精神病。”呵,小小年纪,看人倒是很准呐,也不当面说说,我好尽早治疗。
高二时,我厌学到飞起,同学们就打赌我沈阳市期末的数学考试是不来考还是考砸。当时的班级第一笑嘻嘻地告诉我,不过后来他在大学也确诊了双相,休学,曾经四天四夜未合眼,也曾自杀未遂住了院。
我起病要追溯到初二上学期。
晚上突然没有办法正常做作业,天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做梦也都是在做作业,期末考砸了,被老师和家长轮番辱骂,想死,想跳楼,想象从高楼坠落被风吹刮的感觉。
“八年前去就医了吗?”确诊那天,甘医生问我。
我愣住了,我终于意识到,什么?我曾经有这个选项的吗?
那次缓过来的契机有点搞笑,是英剧《神探夏洛克》出了第三季,《神探夏洛克》都能更新,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呢?
有时,活下去只需要一些借口,哪怕这些借口微小而荒谬。
其实当初发病时并不自知,但劫后余生总归心知肚明,我知道了自己肯定哪里“不正常”,可那时的我太弱小了,我救不了我自己。
往后,每一年,抑郁都会找上我,无一例外,只是程度轻重有别罢了。
从初三开始,就有明显混合发作的特征,我的抑郁开始裹挟着愤怒袭来,我暴食得迅速胖了二十斤,又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一边躁狂一边抑郁,两个恶魔同时撕扯着我的灵魂,可年幼的我哪里懂得这些,我只是痛苦,痛苦又痛苦。
高一,我做了心脏的手术,预激综合征的射频消融术,我变得很偏执,如果老师讲课不合我意我就觉得他们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心脏的问题很早就出现,但也是在初二上开始恶化的,那时我跟妈妈讲,妈妈把一个不锈钢碗扔到我的脚边,“你一个小小孩儿有什么心脏病,你就是知道我有心脏病,你气我!”刚上高中,作息变动巨大,我的身体不适应,发作了,连续一周心率高居不下,我却撑着连间操都不肯请假,我告诉了姐姐,姐姐“告密”后爸妈才知道。确诊那天,我在医院的洗手间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年轻小姑娘天真的脸已经被疾病折腾得毫无血色,夸张到嘴唇和面颊已经融成一个颜色。但那时心底涌出一股矛盾的开心,原来我不是无病呻吟,原来我的痛苦事出有因,是你们错了,你们大错特错。而这种感觉,我竟也要体会两次。
我的世界再次崩塌,是高二上学期。
姐姐第一年高考失利,转战复读,于是这般焦虑和恐惧从我初三末期起一直笼罩我到高考当天。我怕我也高考考砸,我怕我也复读。高二分文理后开学第一天,中午我回家拿着高一下学期期末九科年级大榜把全班同学的文科六科成绩算出来,我第三,我觉得我完了,上不了北大了。晚上,从第一节晚自习我就开始哭,哭了一个多小时,又不能打扰到别人学习,我不得不哭得很克制,当时我还不知道,往后这两年,我经常这样很克制地哭。之后我就不上晚自习了,天天回家哭,任凭泪水滑过脸颊,就让悲伤把我淹没吧!学习再次变得很困难,我又总觉得我学不完了,又抑郁又焦虑。我上课也经常哭,在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课上我都哭过,却从来没有一个老师问我怎么了,我不乞求他们上课停下来关心我,但下课也不看看我怎么样真的合适吗,我就坐在第一排,怎么会看不见。我还会逃课去操场哭,有一次逃了数学课,哭了半节课哭好了,想回去上课,结果发现门锁了。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处理的了,我应该没有勇气敲门进去吧,是提前去吃饭了,还是转身去操场了呢,我已经不记得。
太痛了,高二上像“断片”了一样,我记得我天天哭,有这件事,但都没有画面了。我忘记了很多事情,和普通的遗忘不同,普通的遗忘提醒了总有些印象,这样的遗忘线索全无。
有个学长抑郁留级到我们班,只念了高二上,然后就去加拿大读高中跟大学了,2021年见他,他聊起很多往事,我完全不记得。他只拿了诊断,并未治疗过,听他说,他发病的时候会从心脏往外浑身疼,于是他用力扯自己的头发,后来索性就剃了光头,我看着他坐在我对面笑着对我说,留给自己四年时间,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死了。他的笑,比哭还要悲伤啊。
如果说我是一座孤岛,那我们就是一座又一座孤岛,连不成大陆。
这一轮抑郁一直弥漫到高二下,直到学长学姐的沈阳市二模出分,有一个学长的父亲晕倒后头磕到电视机角去世了,我忽然觉得,我不能就这么活。
于是,某个周末,我瘫坐在出租屋的门口,带着哭腔跟爸妈苦苦哀求:“求求你们,放过我!”
强势的爸妈暂时地放过了我,但命运没有。
03
“老师,您啥时候有空啊?有点想找您聊聊。前一阵子去看了精神科,我知道心理治疗得找别人,不过还是想听听前辈的看法吧。”
2021年10月17日,在马路上,我忽然像溺水一样,胸闷,喘不过来气,想起不好的事情,想哭又哭不出来,忽然想起来了昕老师,2020年初他在组织行为学的最后一节课上说过,“你们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没有钱了我请你们吃一个月饭都没问题的。”那……这样的事情应该也可以吧。反复检查,忐忐忑忑,点击发送。没过几分钟,老师就回了我消息。
遇见昕老师是在大二上,又一轮剧烈的发作期,此时已不是单纯的抑郁。那一年我的脾气很坏,朋友后来形容我是一点就炸的火药桶。睡眠很差劲,我开始擅自服用褪黑素,可是慢慢吃了褪黑素也要四五点才能睡着。白天喘不过来气,晚上睡不着觉,就是在那样的情况遇见了他,可能黑夜里也孕育着黎明。
“昕,旦明,日将出也。”
又是一个美丽的名字。
大四上开学初,高数补考理所当然的又挂科了。现在想想并不意外,其实已经发病了,看见昕老师会躁得难以入眠,平时又焦虑到没有办法在人多的打印店打印一份论文。当时就想,回家看病(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在人多的地方待着),如果确诊了抑郁症就休学治病。
2021年9月26日,那天我早上九点半才睡着,正常发挥,一个人走进了诊室,反复盘算的病史却突然说不出口。
我没有办法跟一个陌生人承认,我13岁就抑郁了,我13岁就想跳楼,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只能说我从2019年开始失眠,这样听起来更像一个正常人吧,应该吧。
听我说我看两台春晚后都躺在床上半哭不哭的,那个医生笑了。我感觉被冒犯了。
“你有没有特别兴奋的时候?”
我知道她在问什么,“没有!”
“加一个量表,我们要排除一种可能性。”
“是双相吗?”
“你还挺懂!”
我当然懂,懂到我随即回避了所有涉及情绪不稳定和暴力倾向的选项。
医生只给出了“焦虑状态”的诊断,我问她SCL-90里抑郁均分4.0怎么解释,“没有抑郁吗,这分儿可挺吓人啊!”她说这是焦虑引起的抑郁情绪。仅仅是抑郁情绪,真的是吗?
“你想吃药吗?”
“不想!”
“那我给你开植物药(圣约翰草提取物片)和中药(九味镇心颗粒)吧。”
都这样了,还不想吃药呢,好像忽然忘了自己这八年是怎么过来了的一样。
此前我和昕老师并不相熟,上一次联系还是因为2021年7月的偶遇,我给他发了消息,他在晚上十一点半回了我两条长语音,我听了就激动得一宿没睡,白天又四处和人说起这件事,哎呀,老师真好,真好真好,标标准准的轻躁狂。
推开教师休息室虚掩着的门,我终于见到了他,把我的故事,从头讲起。我信任的人接纳了我,于是我也可以学着去接纳我。
另一边,学院另一位很好的王老师看我情况不妙也主动约我并劝我继续就医,“要去看医生了,不能隐瞒病情,必须实话实说了,你现在是有很严重的躯体症状了。”当然,我本来是没这个打算的,本想着吃完了手里的药就这么算了,反正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活法。
走到甘医生面前,是我东拼西凑的勇气。
终于,我颤抖着声音从2013年开始说起,依旧否认,依旧瞒报,但也给了甘医生足够的信息。
但,双相情感障碍,这六个字无异于晴天霹雳。
为什么?为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老天爷啊,你不公平!恶人平安无事,我又没有去害人,你凭什么把这般灾殃降在我头上!
借着早上喝的咖啡,我开始了快速循环,迅速转相,大起大落,痛苦,挣扎,一猛地扎进了漩涡里。
我又找到了昕老师。
第二天,他在上课和指导博士论文的间隙抽出来半个小时和我聊天。
前一晚刚吃下半片阿立哌唑的我还昏昏沉沉。
“我觉得你没什么问题,就是情绪不太稳定啊。”
后来才知道其实他对双相没什么了解,不过歪打正着的安慰起了作用。
04
确诊后,我搜到甘照宇医生写过一本科普书籍《双面人生:双相障碍解读》,马上下单买来看,竟颇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也理解了他问诊时的一些话是什么意思。
“你每天都抑郁吗?”
“不是,它偶尔会给我放几天假。”
这是快速循环。
“对了,我抑郁的时候会强迫自己运动。”
“什么,你还运动?”他当时眼睛都亮了,唯一一次没控制好表情管理。
这是混合发作。
后来我才知道,快速循环、混合发作外加饮食问题和生物节律问题也是他首先为我挑选阿立哌唑的依据。
了解真相很快消解了病耻感,书粉甚至想着复诊一定得要个签名。
但,天不遂人愿。
抢不到号,但我药就快没了。其实是听说过能加号的,但我太害怕麻烦别人了,想想就觉得可怕。
总听人说,在精神专科医院能接受到更加充分的治疗,看了眼那边又是号源充足,就跑路了,那边的医生加了碳酸锂。
寒假在家看了一次,医生说是“药源性焦虑”,减了阿立哌唑。大四下选择延毕后就没有回来,爸妈不想让我看病,就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去精神卫生中心区级院区挂号开药。
半年多没有复诊,回来后专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做出了误判,把轻躁当成了焦虑,开了抗焦虑药坦度螺酮,又用鲁拉西酮换掉了阿立哌唑。
于是,我转躁了。
毁天灭地的那种。
好消息是,我被辅导员带回到甘照宇医生的面前了。
当然是好消息,躁狂归躁狂,签名得要。
终于是又见到了,这是2022年10月5日,迟了快一年。
坦度螺酮和鲁拉西酮让我转躁,碳酸锂不适合我的快速循环型——三种药,三种都不合适。
“这么断断续续地治,要不住院吧。”其实我只记得后半句,太亢奋了,前半句还是辅导员告诉我的。
第一次的门诊病历写了“自知力欠全”,第二次的门诊病历则写了“自知力存在”,我一边发病一边给辅导员解说这都是什么症状,非常朋克。
几经周折,终于在第二天晚上住进了医院,爸爸从东北过来陪护。
26天。
我最终在里面住了26天。
翻了翻日历,我才意识到,一年有12个月,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彻头彻尾地在当一个病人。那时我刚22岁,却已经有9年耗在这个病上。
在那9年里,我就像西西弗斯,循环往复地推着一块巨石,苦苦攀登,又在一瞬跌入谷底,向着高处却又无法抵达。
我是一个英雄,可我的英勇又是那么脆弱和荒谬。
05
第二次见阿甘(微博上的患者们都喜欢叫甘医生“阿甘”)之前,我就自知“凶多吉少”,这次大概是要住院了,便把衣服都洗出来了。可真的听到这个消息,也并不是很容易接受。
本来就约好了看完病找昕老师聊天的,跟他说,行程有变,入院14天。不过如果他有空,就第二天再住院吧,恰好我又在快速循环,没有力气。他看见消息很着急,主动提前了聊天的时间。
我见到了他,他满眼的愁容与担心,他一向意气风发,一切尽在掌控,我自然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他放我走还是因为辅导员打来视频电话催我收拾行李办入住。
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很是神奇,我本只是个没什么关系的本科生,如今也是个重要的存在了。
我原来很喜欢在知乎看一些“在精神病院住院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熟悉得就差自己住进去,真到自己住进去倒觉得是一种疗愈。
不,不只是疗愈,那该是我此生的滋养。
很多人最怀念高三,我不会,高三时还会有同学希望你考得没他好呢。但病友间的利益冲突就要少多了,在医院里,所有人都希望你好,外面很少有这样的情形了。
病友们都很好很好。
有一个自杀未遂过六次的姐姐如今心态很平和,大前辈了,她有很多的方法论来劝大家。把树想象成椰子树,我们是来海南度假的!她得病的年纪和我现在差不多,也不知谁更苦一点,也或者,里面的人都很苦,这里不需要痛苦的奥林匹克。某次在大铁门看到一个10岁的精分哭喊着要回家,夹杂着我听不懂的潮汕脏话。
该如何形容这里面?
苦难的集合,勇气的赞歌。
婧来的第一天就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好喜欢你,我对你一见如故。”
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很相似,比如都喜欢诗歌,比如都有改变人生的老师。削减独特性会有些别扭,不过也说明我们其实并不孤独,孤岛也并不是真正的孤岛,我们在更深刻的海底血肉相连。
她的躁狂比我的还要凶险得多,既有幻觉又有妄想(我只偶尔有一点未达到诊断标准的妄想),擅自停诊断药的经历让她的疾病不断发酵。
某次阿甘带队查房,我拉着她给阿甘喊应援口号:妙手回春甘医生,双相杀手甘医生!治病救人甘医生,和蔼慈祥甘医生!(婧的记忆力受损,她只喊“甘医生!”)
阿甘一边摇头一边走向8床一边说:“太躁了,太躁了,哎呀!”8床妹妹举报了我们:“她们排练了好几次!”不过我们没有举报她——她也有一个应援口号来着:阿甘教授帅气的脸庞,阿甘教授中山三院称王!
阿甘很受欢迎,当然,不只是阿甘,三院的医护都很有爱,他们给予我们克制的善意,温暖而不会灼热。
某次查房结束,我的管床医生彤彤非常着急地跟阿甘说——她都不写公众号了,微博也不发了!(因为鄙人的话多体现在各个方面,她暗中观察而并不会与我互动。)煞是可爱。
临近出院,负责测智商的那位医生组织起了读诗会,她来找我时竟然叫出了我的名字,要知道,上一次接触已经是21天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默默关注着我,或许我被给予的善意比我感受到的还要多。
06
XX学校是我的噩梦,至今我还会梦到喘着粗气醒来然后嚎啕大哭,我对着虚无的过去大喊大叫,无能为力。
高三,十一假期回来,隔壁学部的一个男生跳楼身亡,我的班主任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他上课叫同学回答问题,如果同学回答地不合他意,他就说:“XXX,你把窗户打开,你跳下去!”
当时我脑补了自己冲出座位到打开窗户再到落地的全过程,有非常强烈的跳下去的冲动。
昕老师说:“教师队伍里还有这种人!”
阿甘说:“他为什么说这个话?”
我知道,他们至少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前几天刷到一个中学同学的微博,一直没同班过,也不熟,但看她在韩国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真为她感到开心。因为我得过心脏病,高三时的某一个周六(高三的周六要上学),她过来问我心脏不舒服要不要去看医生,我劝她去看,一看不得了,她是厌食,在ICU就住了一个月。
有时就想,医学生实习也不必去什么精神科病区,来XX学校就好了,走一圈就能把精神障碍认得很齐全。
XX学校有一个蛮出名的学长叫郑执,他是一个作家,在作品里反复地写着自己纠结拧巴的青春期。他说:“我青春期最剧烈的精神困苦,就在那几年。”他写精神病拿了奖出了名,《仙症》,这叫法比“精神病”好听,那篇小说加入了他连续三个月不说任何一句话的真实元素。
我们下了苦功走进东北育才,又要用尽力气去走出。但病的是这个系统,不只是我们。
住院时,阿甘跟我说:“只有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后来他又很毒舌,“守着一堆垃圾怎么能捡到宝呢?”
如今我可以很平静地提起那些黑暗的日子了,记得2021年初我跟朋友聊东北育才还会不自觉地声音发抖、手脚冰凉、心脏发慌、心跳加速,仅仅是聊到都痛苦呢。
另一个校区同级一个班里,一个女生长得不太好看,她的班主任就把她的照片打下来贴在墙上,谁犯了错误就去看着照片面壁思过,那个女孩后来转学了。我去跟后来与我同班的同学求证了这件事,他讽刺道,叫这个班主任是老师,有点过了。而这个同学也在高三确诊了抑郁,抗抑郁药让他昏昏沉沉,却也不起什么作用,他高考成绩也不理想,后来几年治疗断断续续。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中学没去治疗是走了弯路还是侥幸逃过一劫(而且谁知道当初会不会按抑郁症去治),索性不再去想。明明我也没有赶上最坏的境况,但我还是病了,并且病得不轻,我的整个青春都浸泡在双相情感障碍里,最应该留下美好回忆的日子,我都在痛苦挣扎。直到某天和朋友聊天我突然想出来一句话:我不希望别人把我的苦难看得太轻,也不希望我把自己的苦难看得太重。所以,以后的日子,轻装上阵吧。
我喜欢说,病人,病人,普通的医生只看到病,合格的医生治的是人。阿甘当然是超级好的医生,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完整的人。但阿甘也不是神医,毫无疑问,我现在仍然是一个病人,会躁,也会郁。但每次复诊他跟我说的“进步”也确实不是骗我的,我在努力,他也在努力。
2023年初的冬天,我久违地在冬天不想去死了,简直是不可思议,要知道我2014年初就想跳楼了。原来平静的冬天是这样的,确实很久没体验过了。
我的生活就像这篇文章一样,轰轰烈烈地起笔,最终只是归于平淡,但归于平淡就很好了。2013年起病,到2023年,10年,好像没什么太多能坚持10年的事情,我却在坚持生病了。但其实双相也教会我很多,教会我珍惜快乐、珍惜帮助、珍惜爱。
高三下学期,我抑郁和焦虑得一周一周地不去上学,就在家里看羽生结弦滑冰的视频。那时每天都看他,没勇气上学时看,学累了也看,需要内心平静时继续看,我很喜欢羽生结弦,我还把他写进了高考语文作文里。羽生结弦说过:“曾经有许多艰辛之事,但没有不拂晓的夜晚。”
我很感激的两个人,他们是不灭的光亮,一个是宇宙的恒星,一个是盼来的黎明。
但有一天,我也会活成自己的太阳。
我还很喜欢一部关于双相的百老汇音乐剧《近乎正常》,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正常,那么近乎正常也可以,那部剧也有一个唱段《光》。
当长夜终于到尽头
当黎明绽放在窗口
你会笑话自己茫然彷徨那么久
眼前那熟悉的绝望
有光就变得不一样
把它都照亮
一天一天
走向自己的愿望
就算最黑的长夜
也能等到朝阳
熬到长夜的尽头
就会有光
尾声
第一次看《深海》的时候哭了好久,因为想到也有人会魔法,他们也为我劈开大海。
我想我是爱他们的,当然,无关风月。
那反过来呢?
医生是有大爱的人,一直坚持做科普,又是2020年广东第一个援鄂心理医生。老师也是有情怀的人,江湖人称“X院男神”,一到毕业季就成为合影景点。
可轮到具体的我呢?
原来我自己用这样的表达会很惶恐,但我的心理咨询师说了“爱”跟“双向的奔赴”,想一想,是爱准没错,大概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珍惜。
被给予温柔的力量,回头看向干枯残破的过往,我也用温柔而有力量的目光。
干枯的枝干上抽出小小的嫩芽。
是,生命啊。
(文章图源:摄图网)
本内容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作为疾病诊断及治疗依据,请谨慎参阅。